
编辑|观星
“报效议叙”即以“报效”的方式获得议叙,其典型是盐商报效,即《清史稿》所言“余如各省盐商、士绅,捐输巨款,酌予奖叙”。
以盐商、广东行商与地方富绅为主的“报效”指向政府捐献财产,这类捐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捐款数额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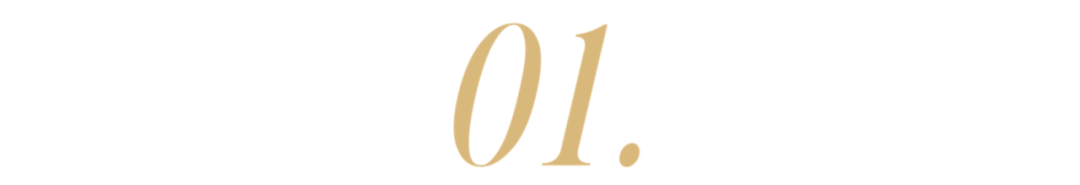
“修理文庙营房”指因捐修文庙、营房等事务而获得议叙,与《清史稿》所载“其乐善好施例内,凡捐资修葺文庙、城垣、书院、义学、考棚、义仓、桥梁、道路。
或捐输谷米银两,分别议叙顶带、职衔、加级、纪录有差”属于一事,所言“乐善好施例”即雍乾之际形成的针对臣民捐办地方公共事务的奖励政策。

其次,《清史稿》所列举的“捐马百匹予纪录、运丁三年多交米三百石给顶带之例”系清代不同时期奖励捐输办理某项事务的具体规定。
关于前者,顺治十七年“定文武各官捐助马匹五十匹以上者,记录一次;一百匹以上者,加一级”;关于后者,康熙四十六年议定“运丁运米三年,多交米一百石者,给九品顶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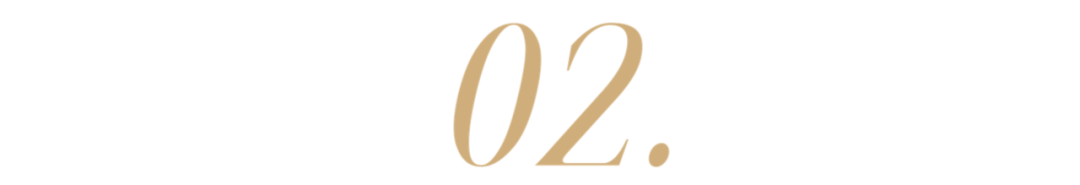
《清史稿》所载未标注时间,与这里所引之例有一定差别。实际上,此类规定很多,清政府对捐办某些具体事务一直都有明确的奖励规定,存废不一。
兹摘录雍正《大清会典》相关规定。这类规定属于捐输议叙的条款,与捐纳事例不同,最直观的差异就是这些规定基本是区间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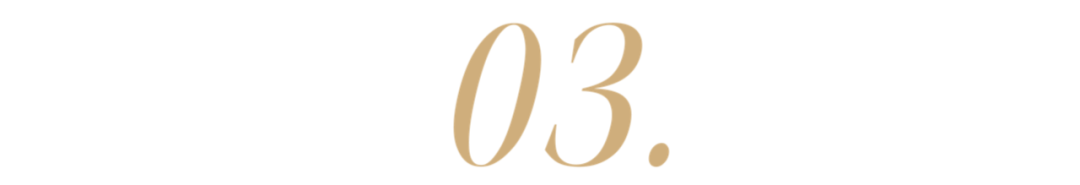
最后,陈锋、薛瑞录、何烈等研究者所论官员的个人捐助,除在战时军费筹集中较为常见外,亦广泛存在于前述各类具体事务中。
谢海涛所列举的十余种名目中,“捐修城工”“捐修文庙”“捐输义谷”属于捐办地方公共事务,“捐输团练经费”“捐输船炮”“捐垫勇粮”属于捐输军需。
所谓“守城出力”“垫办军需、犒师助剿”之中若有捐资,自然也属捐输军需。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捐输军需,即咸同以降的“捐借”“劝借”“捐借兼行”。

该举措主要针对富家大族,始于咸丰三年,最初只行于山西、陕西、广东等省。
具体办法是地方官府向富户“示以筹款成数,然后按照借数,出给印票,分年照数归还”,而且还对捐款者授予功名、封典或匾额作为奖励。
咸丰七年后,该办法进一步推广至江苏等省。彭泽益认为这种举措本属内债,然而政府起初的偿还承诺并未兑现,或在军事结束后“由官府奏请给奖”。
或“请照章加广本省学额”,从而“这些内债便只好由原来的借债人以全数捐助军饷为名,都变成了所谓‘绅富捐’”。换言之,这类款项在实际运作中最终被动变成捐输。
综上,既有研究论及的上述行为均属笔者界定的捐输。根据事由可将捐输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捐输军需,主要体现在战时捐饷银和捐马匹、弓箭等军需物资。
二是捐输皇室事务,主要体现在巡幸、庆典和皇家工程;三是捐输地方公共事务,这类捐输涵盖很广,包括所有与地方民生福祉相关事业,难以一一列举。
其中最常见的是赈济、地方仓储积贮、善堂善会、地方公共工程。
一、广义捐输论中的非捐输举措在上述各类捐输之外,一些从属于广义捐输论的举措虽冠以“捐输”之名而实非捐输。一是清代长期存在的地方官员集体“摊捐”。
乾隆朝以前地方官员的摊捐多称“捐俸”“捐俸工”,乾隆朝以降多称“摊捐”“捐养廉”。
这类举措亦称“捐输”,是地方政府应对公费短缺的常规做法,往往是对通省官员法定收入的直接摊扣。地方官员集体摊捐与官员个人捐输存在差异。
因为针对后者清政府亦会酌情奖励,而前者基本没有获得奖励的可能。此类摊捐本质上是国家对官员法定收入的直接克扣。
二是咸同以降泛滥的“厘捐”等捐税。对此,日本学者织田万等在20世纪初组织编纂的《清国行政法分论》有很好的分析。
该书认为咸丰朝以降之厘捐等实属赋税,系“假捐输之名,避加税之嫌”。
该书进一步分析称:“今清国捐款,多立为公课,勒行征收,其犹名为捐者,盖欲使人民分担国费,以表报效之义也。然其于捐之本义,仍不相合。要是借名义捐,以图免聚敛之讥而已。”
此类捐税绝不可视为捐输。咸同以降以“捐输”为名的捐税繁多,在此仅针对前述广义捐输论提及的名目略作解释。其一是四川的“捐输津贴”。
这种捐输以四川通省按粮摊派的方式进行,可以追溯到乾嘉道时期临时而偶发的战时军费筹集,咸丰朝起变为持续的田赋附加税。
清政府将其称为“捐输”,是为了消解加赋对国家合法性的损害。
其二是江苏等省的“亩捐”,同治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已明确声明其性质为“加赋”:“查亩捐名目,初因军兴支绌,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即是加赋。”
总之,此类田赋附加税只不过是政府借“捐输”之名行加赋之实。三是同光时期的“欠饷抵捐”。
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咸丰时期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兵勇,同治时期战事缓和之后清廷陆续裁撤兵勇。清廷所欠兵勇的军饷无力全额支付。
因此授意将“各省兵勇积欠饷数,一例报捐,请旨加广乡试文武中额”。即政府将所欠兵勇的饷银计入相应省份的捐输款项,以换取该省学额的增加。
这种行为属于“捐输广额”政策的一部分,兵勇实际未曾缴款,只是政府以“捐输”的名义解决无力发放军饷的困境。
至于捐输广额政策,即咸同以降政府为筹款而合计一省、一府、一县的各类“捐款”总额予以增加学额的政策,实属复合制度。
其奖励针对的款项主要包括捐纳和捐输,此外有时也将捐税等款项计算在内,因此捐输广额政策所针对的款项涵盖十分宽泛。
二、误区澄清与前景展望捐纳属于清代的法定制度,是一种历史概念。伍跃将其准确界定为:“政府出卖各种与做官有关的资格。”
而捐输更多是一种现代研究概念,因为清人既用“捐输”称呼各种与“捐”相关的行为,又对属于捐输的行为赋予捐助、输助、报效、乐捐、乐输等多种称呼。
更多情况下只是描述行为而仅称“捐”。此外,清代捐纳、捐输概念混用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输”“纳”语义相近,清人有时使用捐输、捐纳作为动词描述行为。
因此史料的字面措辞无法反映制度内涵和实质;二是捐纳属于卖官鬻爵而声名不佳,政府为了避免指责,捐纳者为了掩饰,都时常将捐纳讳饰为捐输。
三是清政府对捐输的奖励往往参照捐纳事例,尤其是嘉庆朝以降政府往往比照捐纳事例制定捐输细则,导致特定捐输与捐纳高度相似。
四是咸丰朝以降政府筹款时经常将捐纳、捐输、捐税等并举,而且以“捐输广额”制度奖励各类应急款项,从而当时人也就将各项筹款措施笼统称为“捐输”。
《清史稿》罗列了一些“与捐纳相似而实不同”的捐款行为但未做定性,许大龄最早辨析捐纳与捐输的差异但区分标准不够具体。
行为主体、捐款事由三项次要差异区分二者,并将捐输准确定义为:“臣民并非出于义务地将财产直接或间接捐献于国家的行为。”
在上述总结的基础上,在此对若干疑问略做反思性的分析。
第一,行动者自愿与否、所得是否实官,能否作为捐纳与捐输的区分依据?既有研究普遍认为捐纳出于自愿,对捐输出于自愿还是强制则争议较大。
在制度运行中,二者均为自愿与强制并存。总体来看,除盐商、行商等特权商人的捐输始终属于强制性的集体摊派外,一般臣民无论捐纳还是捐输名义上都应出于自愿。
在国家财政紧张时,尤其在咸同以降“勒捐”“派捐”成为常态,这种强制捐款既有捐纳也有捐输。
至于收益问题,不少研究者将是否授予实官作为区分标准,认为只有捐纳才能获得实官,捐输多属无偿捐献或只是荣誉性的表彰,因此在收益上捐纳比捐输更合算。
或者认为在清前期捐输基本是奖励虚衔、封典等荣誉性资格,咸同以降才给予实官,由此导致该时期的捐输与捐纳即是同一制度。这类认识都是不确切的。
由于捐输议叙可以参照捐纳事例,因此自然可以获得实官。从大量案例来看,捐输奖励实官的现象在清前期已经存在,泛滥于晚清。
第二,嘉庆朝以降由政府颁发详细规则的特定捐输,能否与捐纳区分?如前所述,早在清初政府就已经为某类捐输明定奖励规则。
不过就笔者所见,直到嘉庆朝的“河工投效”,政府才在明定奖励规则之外,又详细罗列举办时限、收款机构等细则,而且这种细则就是比照捐纳事例制定。
清人已认识到此类捐输与大捐的疑似问题。嘉庆十一年,御史杨昭反对户部比照捐例制定南河投效方案。
他认为朝廷才于白莲教战事平定后停止大捐,“续又援照捐例议叙投效人员,分班选补,是固无开捐名色,而终不免有指捐情事”。
而且政府对捐输的奖励“久有成宪遵循,似亦勿庸援照捐例方可办理”。他认为此举有以捐输之名行捐纳之实的嫌疑。
对此嘉庆帝辩称:“向来本有捐输议叙之例,今既准其在部呈交,若不明定条款,则议叙时未免无所遵循。并非甫经停捐,又特开捐例也。”
随后户部遵旨拟定“南河捐输料价议叙规条”,详细开列了举办时限、收款机构、铨选班次、项目及银数、执照、印结等规则。
数日之后,嘉庆帝在略作修订后批复同意这份比照捐例制定的捐输“规条”。本次河工投效的细则比照捐例制定,因而在形式上与捐例高度相似,但实质却有显著差异。
其铨选班次的规定为:此次奏请捐输报效,与各例报捐人员,本属有间。如捐输果能踊跃,其铨选班次,自应较各例捐班,量予从优。
惟现在议定条款,京官以郎中为止,外官以道员为止,武职以参将为止。
其现任及现在议叙郎中、道员、参将等官,或情切急公,其捐输银数,迥逾于现定议叙条款者,应由户部核其银数多寡,会同吏兵等部,专折奏请特恩,量给升衔优叙。
首先,政府明确声明本次“捐输报效”与“各例报捐”不同;其次,政府声明本次捐输铨选班次要比各项捐纳班次从优,而且可以通过专折请奖的形式突破捐纳对最高可得官职的限制。
这种捐输收益不由“规条”明定而是临时酌定;最后,捐纳事例规定了各项资格对应的固定款项数额,而这份捐输“规条”所载银数只是参考。
或说只是获得议叙的最低数额,政府鼓励捐输者捐出超过“规条”的银数。
第三,咸丰朝以降捐纳与捐输是否合流,或者说捐输是否已经捐纳化?合流论以白莎为代表,她认为咸丰朝以降二者趋同。
捐输获得了与捐纳一样的铨选资格和班次,二者在收款机构和筹款目的方面的分野不复存在。此外,广义捐输论、捐输等同于捐纳论也基本可以归入此类。
因为这些研究多是在论述晚清时期。以上三种论点的实质可以归纳为晚清捐输的捐纳化。
作为清代同时并存的两种筹款举措,制度相对成熟的捐纳影响到捐输的制度变迁本在情理之中。
三、捐输与捐纳清前期政府议叙捐输时就往往参照捐纳事例,捐输者同样可以像捐纳一样获得实官,这种做法在乾隆朝愈发普遍,多次引发关于“捐输疑于捐纳”的讨论。
这种质疑源于已经无法仅从所得资格区分二者;政府进一步直接比照捐纳事例为特定捐输制定细则的做法起于嘉庆朝并泛滥于道光朝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咸同时期.
这种捐输细则与捐纳事例在形式上高度类似。即便如此,捐输并未因此与捐纳无法区分,二者的差异仍然存在。
部分晚清史的研究者之所以将咸同以降的捐输视为捐纳,既是因为该时期捐输在某些方面与捐纳高度相似。
又是因为咸同以降的史料中确实普遍将捐纳、捐输、捐税等筹款举措泛称为“捐输”,背后还有更复杂的财政背景和社会背景。
一方面,咸同时期政府迫切需要解决太平天国战争引发的财政危机,至于筹款名目的区分并不重要。
具体而言,在中央财政管理陷入混乱的局面下,地方政府甚至统兵将帅往往自行设置“捐局”筹款。
这类捐局冠以筹饷、防堵、军需之名,或概称“捐输局”,所收款项不仅包含不同名目的捐输,而且往往就近一并代收常捐和各项大捐,最终以“捐输”为名统一汇总。
另一方面,在咸同以降国势衰颓的背景下,政府更忌讳捐纳的恶名,频繁开办的大捐又导致捐纳筹款效应的递减。
与此相反,捐输既具有话语上的道德正当性,政府又可以在比照捐纳事例推行捐输的同时以“从优议叙”“特旨请奖”的策略鼓励大额捐款,由此极大地拓宽了政府的财政汲取范围。
换言之,咸同以降政府确实有以捐输之名行捐纳之实的嫌疑,名实的分离增加了区分的难度。
捐输捐纳化的嫌疑始终存在,并不是晚清时期才有的新问题,只是说嘉庆朝以降尤其是咸同时期愈发突出。
特定捐输在某些方面与捐纳有相似之处,但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合流,更不能因此认为捐输等同于捐纳。
尤其是,并非所有的官办捐输都是比照捐纳事例制定细则或参照议叙,更不用说大量的民办捐输了。